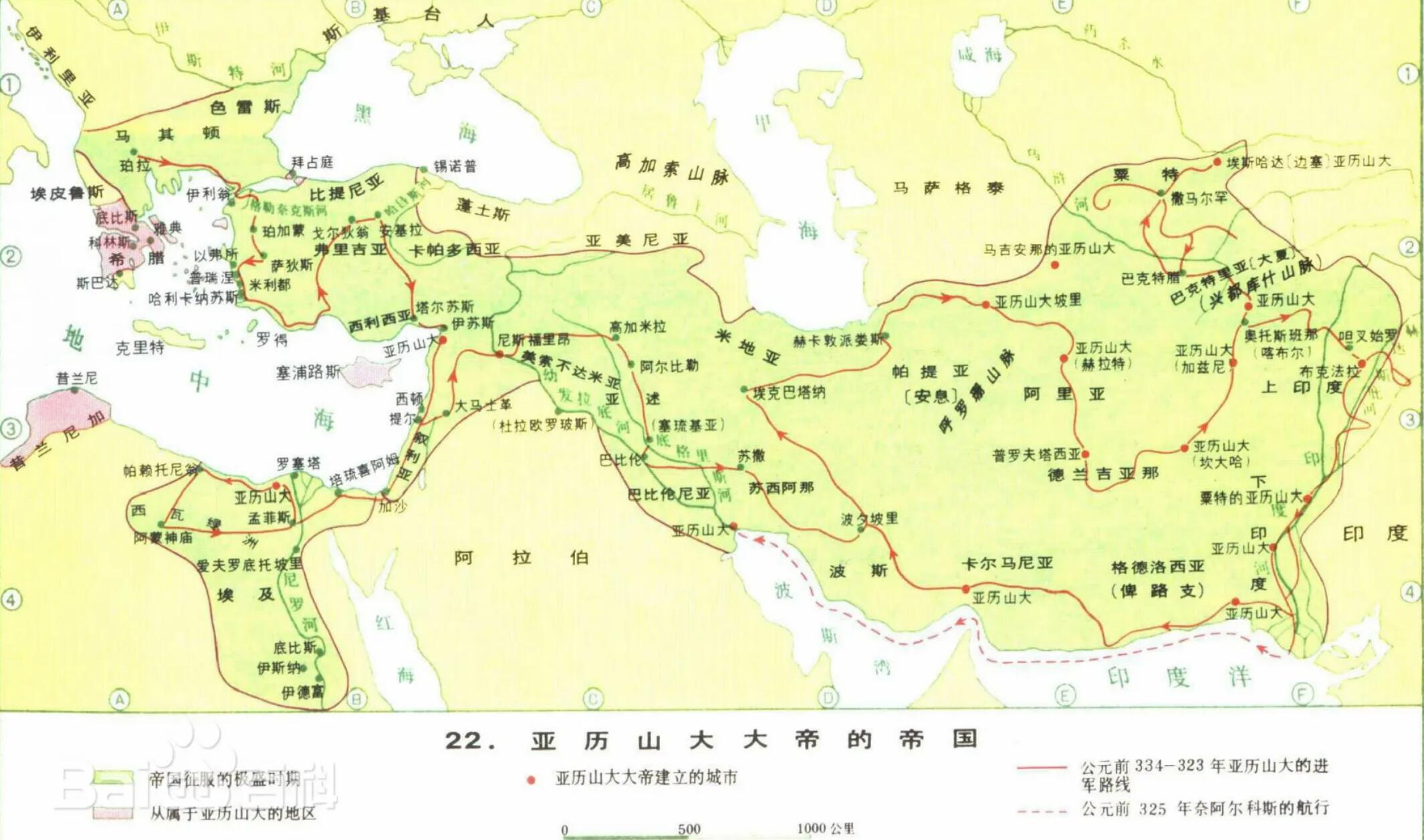宋孝武帝礼仪改革与南朝陵墓新制的形成
耿朔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陵墓既是想象中的超越性空间,也是现实中的政治性空间。丧事的处理似乎带有天然的社会性,对家庭、家族来说,为故去的成员举行丧事,不仅是为了寄托伤逝之痛,对内凝聚和激励人心,丧事活动的具体内容也是对外展示实力的的有效手段。对一个王朝或政权来说,要对整个社会进行充分管控,丧葬领域不可忽视,设计什么样的丧葬等级体系以及如何去实践,是其统治方式的生动体现。以帝王陵墓为代表的高等级墓葬更成为一种象征符号,通过物质材料的选取、空间环境的营建以及视觉语言的塑造传递特定的丧葬观念与政治意图。在对中国古代墓葬的研究中,学者们早已注意到凝聚在陵墓这种物质遗存之上的丰富信息,如关于西汉帝陵陵园的空间模拟对象是长安城还是汉帝国的讨论[1],又如通过研究以厚礼改葬而建成的乾陵三大陪葬墓,揭示武则天去世后唐廷剧烈的政治斗争[2]。
本文聚焦南朝启幕的刘宋时代。在以都城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南朝统治核心区,虽经考古发掘能够归属刘宋的墓葬数量还不多,也还没有发现明确的刘宋帝陵,但从被推断地处刘宋岩山(又名龙山)陵区的隐龙山墓地等材料来看,南朝早期的高等级墓葬与东晋相比已经发生显著变化,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新要素出现得很突然,并在此后整个南朝时期得到持续发展。此前已有多位学者对此加以总结和分析,王志高指出大约从刘宋中期开始,墓葬结构出现新的因素,如设置石门和石质葬具,墓室侧壁及后壁开始向外弧凸但尚不明显,这些标志着南朝墓制的初步确立[3]。韦正认为南朝墓葬中最具代表性的装饰艺术——竹林七贤砖画在刘宋时期已出现,而且刘宋陵墓相对前朝发生多方面变化,甚至“几乎尽抛东晋成规”,他推测陵墓石刻的使用与刘裕的刘姓及北伐见闻有关,而近椭圆形长方形墓室的使用可能是刘氏对南方当地流行墓葬样式的采纳[4]。倪润安总结了南朝墓葬发生的多种变化,认为以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墓葬新面貌最能体现政治背景的影响,南朝逐渐放弃“晋制”墓葬形制,墓葬特征深陷地方化格局,此现象可以在南北朝墓葬文化正统争夺的视野下予以理解,如陵墓石刻在刘宋建国后不久即出现,是在精神层面制衡北魏的重要措施[5]。
以上研究表明,从礼仪制度视角出发分析刘宋墓葬新面貌是可行的。本文延续这一研究方法,综合整理相关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对建康地区晋宋墓葬演变轨迹展开进一步梳理,揭示墓葬形制、墓内石制品、墓志、神道石刻、墓室壁面装饰几个方面发生改易的背后动因,进而发现宋孝武帝刘骏在位期间进行的礼仪改革直接推动新型陵墓制度的创立。
一、墓葬形制的变化和墓内石制品的出现
如前所述,要想准确把握南朝早期墓葬特征,出发点无疑是与东晋墓葬进行充分对比。因此,我将首先总结建康地区东晋墓葬的基本特征,并梳理百年间发生的阶段性变化,发现其与政治形势之间存在耐人寻味的关联,这就为同样从政治视角分析刘宋墓葬新貌提供了合理前提。
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已在南京及附近地区发掘了几百座东晋墓葬,是该区域六朝墓葬序列中材料最为丰富的一段,并且有纪年材料和墓主身份相对明确的墓葬数量也最多。总的来看,东晋墓葬表现出普遍简素的做法,仅帝王[6]和士族[7]的墓葬便有许多表现,例如东晋帝陵表现出家族葬特点,不设石刻,高等级墓葬的规模尺寸在六朝各时段中显得最小,世家大族墓葬流行的墓志多为砖质。上述现象恐怕不能用财力多寡来解释,而是特定丧葬观念的反映,用南渡后不久于太宁元年十一月(324 年1 月)病卒的陈郡谢鲲墓志上的话来说,现在埋在南方是“假葬”、是权庴,在北方老家有“旧墓”,等到收复故园之后,迁葬回家族旧茔[8],代表了南渡士族的群体性诉求。《宋书·礼志》称“江左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9],而终东晋一世,帝王陵墓和世家大族墓葬也堪称俭省,这是东晋统治阶层持续一个世纪始终坚持的“政治正确”。
南京东晋墓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演变规律也有迹可循,有学者通过考古类型学研究,将南京东晋墓葬主流的凸字形单室砖墓按照形制结构分为前、中、晚三期,时间上将东晋中期明确定在穆帝永和晚期至升平年间[10]。根据我的分析,或可将中期的时间调整为永和中(约350年)至太元之前(约375年),三期的划分大致是东晋早期(317——350年左右)、中期(约350年——375年)、晚期(约375——420年),造成每次演变的动因中最主要的一点应是时局的改变。
东晋早期墓葬一改江东东吴西晋时多室、双室以及单室墓并行的局面,而突然以平面凸字形单室墓为主流,墓顶结构有穹窿顶和券顶两大类。这并非本地墓葬形制自行演变的结果,而是南渡的北人在获得政治强力和礼仪优势的情况下,带来了中原系统的丧葬习俗,是西晋官方丧葬礼制在江南的延续。随葬品尤其是明器的种类和组合发生了更大的改变,南方此前常见的堆塑罐、家禽家畜、粮食仓储加工类模型明器基本消失,替之的牛车俑群、涂朱陶器皿以及墓志等体现出鲜明的中原西晋葬俗特点。政治动荡下移民群体带来的北方葬俗打断了南方墓葬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吸收了后者的一些内容。
大约从穆帝永和中(约350 年)开始,墓葬形制出现较为显著的变化,此前较多的穹窿顶单室墓基本消失,只剩下券顶单室墓一种,面貌十分单一。此外先前常见的砖砌直棂假窗也突然不见,墓壁开始有外弧的迹象,同时墓室后部设砖棺床的情况增多,可见变化主要体现在穹隆顶墓和墓壁假窗的消失,这两个现象都可抽绎出墓葬营建走向简约的意味,构成东晋中期墓葬的基本特征。这类墓葬的流行时间大致持续到孝武帝太元之前(约375 年)。
如果将中期墓葬形制的演变与南北形势变化联系起来观察,会发现这二十多年间是东晋历史上少有的较为太平的阶段,进一步可以说,这是晋室立足江左以来,前所未有的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对北方占据战略优势,并且取得实际成效。这一切即与北方时局混乱有关,更与一代枭雄桓温的经营进取密不可分[11]。自桓温平蜀(347 年)至枋头之败(369 年),东晋对北方形成战略进攻的态势,数度北伐并收复洛阳,或许可以认为正是从永和年间开始,在首都建康出现了一股将回葬故园的愿望转化为实际操作的社会行为:墓顶结构抛弃费工的穹窿顶而全部采用简便的券顶,是因为日后总要开墓迁葬的,不需将墓室建得过高过大,有些墓室的高度甚至把人们直立其中进行活动的可能都排除了;象征地面建筑上的窗户的直棂假窗消失,也反映了此时的墓葬不再是模拟地面居所,而只是灵柩暂时寄托的临时场所,此地的墓葬则不再作为最后归宿。将这样乐观的渴望通过处理生死这种重大人生问题表达出来,翘首期待着回归旧茔那样一个日子的到来,正是受到时局的鼓舞。
枋头之败,不仅桓温望实俱损,于孝武帝宁康元年(373 年)病故,东晋实力也遭受重大损失,再无力组织大规模北伐,必然给希望满怀的朝野上下以心理上的重创。太元元年(376 年)谢安执政,太元八年(383 年)淝水之战,这十年间南北实力又发生了悄然转变,苻坚统一北方对江左政权造成了巨大压力,回迁故土的热情似乎也暗淡下来[12]。大约在375 年以后,假窗重新出现在墓壁上,墓葬整体的形制变化不甚显著,但墓室规模比前一阶段有所增大,砖棺床和祭台更为普遍,许多墓葬的墓壁外弧更加明显[13]。
虽然刘裕领导的义熙北伐一度取得比桓温更大的成就,军中也不乏王镇恶这样“不克关中,吾誓不复济江”的将领,但似乎已经难以扭转整体观念的转变趋势,从随军文士撰写的行役记行文风格来看[14],多猎奇之辞,少伤感情绪,故土可返,但心已有隔阂。
刘裕代晋之后,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南北对峙的格局已经持续一个世纪,江左政权偏安稳固,文帝元嘉之治使得“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15]北人生活方式和观念意识的南方化过程在安居乐业的氛围下几近完成。另一方面,文帝几次发动北伐均告失利,特别是元嘉二十七年(450年)进行的第二次北伐,由于一系列战略上的失误,不仅未略得北魏一寸土地,反而引得拓跋焘顺势大举南侵,江淮六州遭受空前破坏,造成“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16]的严重后果。此后南朝政权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北伐,北强南弱的现实逐渐被接受。改朝换代之后的刘宋统治者也不必再举起司马氏“克复神州”的旗帜才能团结臣民,江左统治策略出现重大调整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可以观察到的是,墓葬形制也在元嘉前后发生了新的变化。
首先,墓葬规模进一步扩大。根据我的统计,建康地区东晋砖室墓长度基本在4-9米之间,以5-8米的居多。 被推测为帝陵的南大北园东晋早期墓长 8.04 米,汽轮电机厂东晋中期墓长9.05 米,富贵山东晋晚期墓长10 米左右,光墓室长度就达7.06 米,它们在建康地区东晋墓中都位居前列。南京发现的多处东晋士族墓地中,墓葬规模与墓主身份地位不完全对称,而家族墓地内部却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可能是与不同家族的门风有关。郭家山太原温氏诸墓规模最大,其中10 号墓全长达到9.38 米,居各大族墓的首位,其余墓葬都长达7 米以上;仙鹤观广陵高氏诸墓规模也颇大,2 号墓、4 号墓都长达7 米多,三号墓也接近7 米;象山琅琊王氏诸墓则明显规模狭小,除了7 号墓为近方形单室穹隆顶这种高等级墓葬外,其余券顶墓长度均在6 米以下,3 号墓、5 号墓为长方形单室墓,长度更只有4 米多,这些墓葬高度多在2 米多,也有数座在2 米以下的;老虎山琅琊颜氏诸墓规模也不大,全长也只在6 米上下;司家山陈郡谢氏诸墓规模较大,长度多在7 米以上,吕家山广平李氏诸墓长达6 米多,其尺寸比等级较高的象山、老虎山墓地要大。即便墓室尺寸不能作为判断墓葬等级高低的首要标准,但依然是个重要的参考,至少可以反映一个时代在墓葬营建上的普遍投入状况。
2010年在南京南郊西善桥发掘的贾东19号墓为平面凸字型单室砖墓,根据出土砖墓志可知墓主为卒于元嘉十一年(434年)豫章郡永修令(相)、驸马都尉钟济之及卒于元嘉三年(426年)其妻孙氏。钟济之出自颍川长社钟氏,孙氏出自太原中都孙氏,都是永嘉中渡江南下的北方望族,他们二人应该都是南渡北人的后裔。这座刘宋县令级别的墓葬砖室全长近7米,放到东晋墓葬体系中接近大型墓葬规格[17]。2011年在南京江宁淳化咸墅发掘了南朝罗氏家族墓,这是一个史书没有正面记载的普通士族,墓葬均为凸字型单室砖墓。1号墓砖室长度应在8.5米左右,根据出土买地券信息和学者考证,墓主为卒于东晋义熙五年(409年)、改葬于元嘉二十二年(445 年)的罗健夫妇,五号墓砖室长度超过9 米,墓主为葬于元嘉三十年(453 年)的罗健之子罗道训。罗健任职晋廷,官至兰陵太守,封刘阳县开国男。罗道训袭父爵,晋末任武原令,宋元嘉四年(427 年)起历任广川令、南广平太守、龙骧将军、左卫殿中将军、行参征北将军事等职,参考《通典》“晋官品”“宋官品”,罗健官职五品,罗道训官职最高三品,因此父子都为中层官员。两座墓葬的长度要明显大于上述东晋士族墓地中一些同级别人物的墓葬[18]。假如罗道训确如学者所考证的,就是《宋书》所载元凶刘劭弑父篡位事件的同谋始兴王刘濬的部将罗训,他很可能在元嘉三十年五月孝武帝刘骏平乱建康时被杀,那么即便罗训有过投诚之举,“故其葬事安排可能得到了一定的宽待”,恐怕也不宜以常情视之,之所以还能营建如此规模的墓葬,大概只能置于墓葬规模普遍扩大的时代风气下才好理解,罗氏家族墓地出土买地券指向了元嘉后期,时在五世纪中期[19]。
2000 年发掘的南京南郊隐龙山三座南朝早期墓,墓主被发掘者推定为陪葬孝武帝景宁陵所在岩山陵区的刘宋皇族。这三座墓葬在形制结构、墓内设施以及随葬品方面相对东晋墓葬都有较大改变,被视为体现南朝葬制的早期典型墓例。三座墓均为凸字型单室券顶墓,光从规模上看就令人瞩目,1 号墓砖室全长9.14 米,墓室内长5.64 米,2 号墓砖室残长8.16 米,墓室内长5.38 米,3 号墓砖室残长也是8.16 米,墓室长方形残长5.384 米[20],由此或可推想景宁陵地下空间更为宏阔。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幕府山南麓地段发掘的两座墓葬,以及1997 年在富贵山西南麓发掘一处六朝时期墓群中的4 座墓葬,被认为与东晋帝陵区关系密切,墓主可能是皇室成员或陪陵的重臣。这几座墓葬基本也都为平面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从规模上看,时代被推测为东晋中晚期的幕府山3 号墓全长6.5 米,其中墓室长4.6 米、宽1.9 米,4 号墓亦为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墓葬全长近7 米,其中墓室长4.93 米、宽1.83 米。时代被推测为东晋早期的富贵山2 号墓全长4.81 米,4 号墓全长6.76 米。推测为东晋晚期至南朝早期的6 号墓全长6.16 米,破坏严重的5 号墓仅存长4.6 米的墓圹。这些墓葬的规格都要小于隐龙山[21]。
齐梁陈时代,帝王陵墓的砖室规模更为扩大。上世纪60 年代在江苏丹阳先后发掘了三座被认为是南齐帝陵的南朝大墓,其中鹤仙坳大墓砖室全长15 米,墓室长9.4 米,吴家村大墓砖室全长13.5 米,墓室内长8.2 米,金家村大墓砖室全长13.6 米,墓室内长8.4 米[22]。2013 年在南京东北郊发掘的狮子冲1 号、2 号墓,被分别推定为梁昭明太子安陵和其生母丁贵嫔宁陵,1 号墓砖室全长14.2 米,墓室内长8.32 米,2 号墓砖室全长15.2 米,墓室内长8.4 米[23]。南京东北郊还多次发现梁代诸王墓,1974-1975 年发掘的甘家巷六朝墓群中,4 号墓墓主可能为梁安成康王萧秀,砖室全长9.5 米,墓室长6.4 米,6 号墓可能是萧秀家族墓,砖室全长10.3 米,墓室长6.3 米;1979 年在尧化门发掘了疑似梁南平元襄王萧伟墓,砖室全长10.25 米,1980 年发掘的梁桂阳简王萧融墓已遭破坏,根据残迹测量墓室全长约9.8 米;1997 年在白龙山发掘了疑似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砖室全长13.4 米,墓室内长7.7 米;1988 年发掘的萧融之子、桂阳敦王萧象墓规模要小一些,砖室长6.48 米[24]。1961 年发掘的被推测为陈代帝陵的南京南郊罐子山大墓,砖室全长13.5 米,其中墓室长达10 米[25]。显然,这些南朝中后期帝王陵墓的规模与东晋相比普遍扩大许多,这种变化应发端于刘宋时期。
墓室两侧壁外弧的现象在刘宋时更为多见,但还只能归入略显外弧的范围,到南朝中后期墓室平面发展为非常明显的近椭圆形,这应当主要是建墓技术改变的结果,至于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目前很难给出可靠的答案。赵胤宰、韦正指出这种墓形是南方土著传统,东晋帝王陵墓不用,北来士族很少用,刘宋采用这种墓葬形制明显是对东晋的否定,实际上认为应在南方本土的丧葬传统中寻找有源之水[26]。这表明墓形选取的背后可能也有政治考量,可备一说。
如果说刘宋时期墓葬规模和形制的演化尚处于“量”变过程,不易把握,那么大约从刘宋中晚期开始,建康地区大中型墓葬突然涌现大量的石制品,就显示出某种“质”变正在发生。石制品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墓葬中的固定设施,如在甬道里砌筑石墓门,一般由门槛、门柱、门扇、门额等构件组成,取代东晋墓葬普遍采用的木门,门额上或雕出仿木结构的人字栱,在墓室前部放置带有四足的长方形石祭台,在墓室中后部砖砌棺床上放置数量不一的石板拼成的棺座。另一类是模型明器,孙吴西晋时期南方墓葬中陶质明器和富有地方特色的瓷质明器并行,东晋以新式组合的陶明器为主,刘宋时期则出现石质明器,包括人俑、屋、灶等模型。目前所见建康地区刘宋或南朝早期墓发现石制品情况整理如下表(表1):
表1 建康地区南朝早期墓石制品情况
墓号或墓名 |
墓主人及年代 |
设置 |
模型明器 |
纪年材料 |
|
纪年墓 |
南京贾东19 号墓 |
永修令(相)、驸马都尉钟济之:元嘉十一年(434年); 孙氏:元嘉三年(426年) |
石弩机1(仅余望山部分) |
砖墓志 |
|
南京江宁咸墅1 号墓 |
东晋兰陵太守、刘阳县开国男罗健:卒于义熙五年(409 年)、改葬于元嘉二十二年(445 年) |
石门(两侧石门柱及石门槛尚存)、石祭台 |
砖买地券、卖地券 |
||
非纪年墓 |
南京隐龙山1 号墓[27] |
出土“孝建四铢”, 刘宋中晚期 |
石门1 、石棺座2 具(每具由2 块长方形石板拼成)、石祭台1 |
俑1 、灶1 、屋1 陶明器、陶俑也有 |
近方形墓志1(只字不存) |
南京隐龙山2 号墓 |
刘宋中晚期 |
石门1 、石棺座2 (每具由2 块长方形石板拼成)、石祭台1 |
|||
南京隐龙山3 号墓 |
刘宋中晚期 |
石门1 、石棺座1 (由2 块长方形石板拼成)、石祭台1 |
俑2 |
石墓志1 (只字不存) |
|
南京尹西村1 号墓[28] |
刘宋 |
石门1 |
俑2 |
||
安徽当涂来陇4 号墓[29] |
刘宋或稍晚 |
石棺座2 (分别由2 块和3 块石板拼成) |
|||
南京栖霞区东杨坊南朝墓[30] |
出土“孝建四铢” “刘宋中晚期至萧齐早期” |
石门1、石棺座2具(每具由2块长方形石板拼成)、石祭台1 |
俑4(因粉化皆仅存人形轮廓, 细部难以辨识) |
石龟趺1,石碑已不存 |
|
南京西善桥宫山墓[31] |
年代争议较大,目前已刘宋中晚期和陈代两种观点比较有影响。 |
石门1、石棺座2具(每具由2块长方形石板拼成) |
石制品出现在刘宋墓葬中应当不是来自技术的革新,毕竟汉代墓葬中就大量使用石材,所反映的是丧葬观念的变化。石材的开采、加工、制作、搬运和安放,显然费时费力,增加建墓成本,而墓葬用石在中国丧葬文化中更有特殊的意义,坚硬的石材使其很早便被视为坚固的保障,如巫鸿在研究满城汉墓最后的石室时指出石材在古人看来是有着永久的作用[32]。从目前的材料看,两类石制品并非同步配套出现,石门、棺床、祭台这类设置在刘宋中晚期大中型墓葬中已较为普遍,这在实际效果层面使得墓葬变为更为安全坚固,而象征意义较强的石质明器似乎还处于萌发阶段,明显逊色于当时依然流行的陶明器,虽然上表中的墓例均已遭盗掘等破坏,但石器一般不会为盗贼青睐。到南朝中后期,石制品的使用更为普遍,尤其是石质明器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甚至成为南朝墓葬文化的重要标志物。另外,在数座刘宋墓葬中发现了石墓志,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下面予以分析。
二、墓志材质和文辞的改易
建康地区东吴、西晋墓葬随葬的身份标志物有买地券、名刺和铭文砖,真正意义上的墓志要到东晋才出现,这是洛阳西晋时期已经较为成熟的墓志文化随着永嘉南渡,移植江东的结果。
就考古发掘的情况看,东晋墓志以都城建康地区最为集中,多为北人家族。碑形墓志在江南尚有发现,但数量极少,如吴县张镇石墓志(325 年)、南京温式之陶墓志(371 年)。张镇出于江东世族,温式之则为南渡名臣温峤之子,授散骑常侍、新建开国侯。前者制于东晋初年,碑阳简介张镇及夫人徐氏,碑阴则简叙家世,多四字成句,尚具铭辞褒扬之风;温式之墓志时代较晚,全叙官职、籍贯、姓名、世系,不见辞颂。除此之外发现的三十多方东晋墓志,形制为长方形和近方形两种,多为砖质,极少石质,砖质偶见特制大砖,而大多数应直接取自砌墓的墓砖,这与中原西晋多石墓志的情况有所不同。再就文体而言,这些东晋墓志内容单纯,不见题额和铭辞,有些字迹颇为潦草随意,交待墓主官职、籍贯、姓名、亡时、葬地、世系等内容,一般仅几十字。少者如南京吕家山李氏家族墓的几方墓志,仅十来字;多者如象山王氏家族墓的王兴之、王建之等墓志达200 多字,但记录的也仅仅是上述几方面内容。墓志既是东晋建立之初礼制建设、巩固统治过程的快速产物,也是反映东晋丧葬活动整体“简素”的标志物。
刘宋前期墓志完全保留东晋风格。南京南郊司家山陈郡谢氏家族墓地6 号墓墓主是葬于永初二年(421 年)的海陵太守、散骑常侍谢珫,墓志由6 块形制相同的砖志组成,每块长33 、宽17 、厚4.5 厘米,规格与墓砖相同,单面刻字,6 块砖上的文字合拼成一篇共有681 字的完整志文,但如此长文依然只记述墓主家世信息,行文风格与东晋墓志无异[33]。在南京铁心桥发现的刻写于元嘉二年(425 年)的陈郡宋乞3 块砖志,每块尺寸也基本一致,长33-34 厘米、宽16.4-16.6 厘米、厚4 厘米,显然也是普通墓砖规格,与谢珫墓志不同的是,宋乞墓志每块行文内容基本相同,重在叙述家族世系和婚姻关系。类似的一式多块现象早见于安徽马鞍山出土的东晋太元元年(376 年)始兴相、散骑常侍孟府君墓,该墓随葬5 块形制、内容相同的砖墓志,只是行文较为简略[34]。实际上,宋乞正是晋人,墓志记载亡于太元年间(376-396 年),距离墓志撰写时间已去二三十年,可能是因为长时间停柩待葬或进行迁葬[35],这3 块墓志保持浓郁晋风实属情理之中。前文提及的南京西善桥贾东19 号墓墓主为卒于元嘉十一年(434 年)的钟济之及卒于元嘉三年(426 年)其妻孙氏,该墓出土6 块砖志,形制尺寸与上述两墓砖志基本相同,属于钟济之的有4 块,双面刻文,属于孙氏的有2 块,单面刻文,字迹潦草,内容近于宋乞墓志,甚至还略去了父祖信息,更为简明。
大约从刘宋中后期开始,墓志在材质和文体两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钟济之墓志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晚的砖志,稍后就出现以石志替代砖志的趋势,这也可以看成是墓葬中出现的特殊石制品。隐龙山1 号墓、3 号墓出土石墓志,1 号墓石志近方形,长36 厘米、宽35 厘米、厚4 厘米,3 号墓石志长60 厘米、宽50 厘米、厚5 厘米,无论从形制还是尺寸来说,都是我们最熟悉的那种墓志类型,只可惜南京地区南朝墓葬石制品普遍用的是石灰岩,极易风化,这两块石志都已只字不存。保存较好的是南京东北郊甘家巷北出土的元徽二年(474 年)员外散骑侍郎明昙憘墓志[36],长65 厘米、宽48 厘米,志文30 行,满行22 字,在叙述完这位出自平原明氏、南渡不久的墓主个人经历和家族信息,赫然出现“其铭曰”三字,后接四字骈文,共有18 句,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西晋洛阳时已经相当完备的更具纪念性意义的铭辞。时间上处于上述考古出土品之间的石志例子,有清末在山东益都发现的大明八年(464 年)建威将军、笠乡侯刘怀民墓志,该志高49 厘米、宽52.5 厘米,因为直题为“墓志铭”而广为人知,迄今也是时代最早的自名“墓志铭”,志文内容铭在前,志在后,颇有特点[37]。从刘怀民的履历看,他出自平原刘氏,又长期在刘宋边境任职,远离建康,未必可以说直接受到都城某种新型墓志文化的直接影响。但刘怀民于大明七年(464 年)去世后,丧事得到中央政府的过问,志文所记的“齐北海二郡太守”“东阳城主”即为刘宋朝廷追赠,考虑在青徐地区找不到这种形态墓志的源头,似乎不能排除刘怀民墓志制作过程有官方参与的可能性。
墓志实物呈现的改变,恰能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大明二年发生了一件关乎丧葬革新的事情,涉及墓志形态的改易,皇弟、建平王刘宏去世,孝武帝“痛悼甚至,每朔望辄出临灵,自为墓志铭并序”[38]。前文已经提及建康地区东晋墓葬出土的墓志,内容上只有志,不见铭,而至此才恢复了西晋洛阳已经很完备的墓志写法。三年后皇太子刘子业之妃何令婉去世,也在玄宫里放置带有辞铭的“石志”。据《南齐书•礼志》载:“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宫中有石志。参议,墓铭不出礼典。近宋元嘉中,颜延之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策,故以纪德。自尔以来,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储妃之重,礼殊恒列,既有哀策,谓不须石志。’从之。”[39]虽然南方这种新型墓志的先声可以追溯到元嘉十八年(441年)前后颜延之为王球所书的石志,但孝武帝的行为具有强烈示范性,不仅作用于当世,也对齐梁陈三代产生深远影响,即便齐武帝取消了在皇太子妃玄宫内放置石志的做法,使用更符合身份的哀册,但是志在王侯和士族阶层依然普遍使用。从考古实物看,刘宋以后,砖墓志极少发现,而南京地区考古发掘的萧融、王慕韶、萧象等梁代诸侯王、王后石墓志便是对“自尔以来,王公以下,咸共遵用”说法的很好注脚。
正如徐冲最近指出,具备铭辞这一纪念装置的墓志,在孝武帝时被纳入了包括皇族在内的整体精英文化之中[40]。
三、神道石刻的设置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地面。相对于深埋于地下的墓葬,墓地的地表建制具有与之相反的展示性。今天散布于南京、丹阳和句容乡间的神道石刻是寻找南朝帝王陵墓的可靠指引。
最早设置石刻的南朝陵墓是哪一座?作为陵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刻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设置的?是否与上文讨论的刘宋中晚期地下空间变化存在关联?这些便是值得讨论的话题。
尚无证据表明能从东晋陵墓制度中寻找到南朝设立石刻的渊源。如前所述,相比秦汉,南渡以后的东晋帝陵规模俭省许多,但肯定设有陵园,考古发现尚未提供线索,可从文献资料进行分析。东晋初,琅邪悼王司马焕薨,元帝“悼念无已,将葬,以焕既封列国,加以成人之礼,诏立凶门柏历,备吉凶仪服,营起陵园,功役甚众。”[41]诸侯王既有陵园,帝陵肯定也有,文献记载了许多在陵所进行的活动,并有“陵令”一职,都说明当时存在陵园。但迄今未在南京发现东晋陵墓神道石刻,文献上也缺乏记载,学术界普遍认为当时确实没有设置石刻。
刘宋陵墓肯定已有石刻。《南齐书•豫章文献王嶷传》有一段话涉及中古陵墓石刻,常被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引用:
(萧嶷)自以地位隆重,深怀退素,北宅旧有园田之美,乃盛修理之。(永明)七年,启求还第,上令世子子廉代镇东府。上数幸嶷第。宋长宁陵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历史迷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历史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