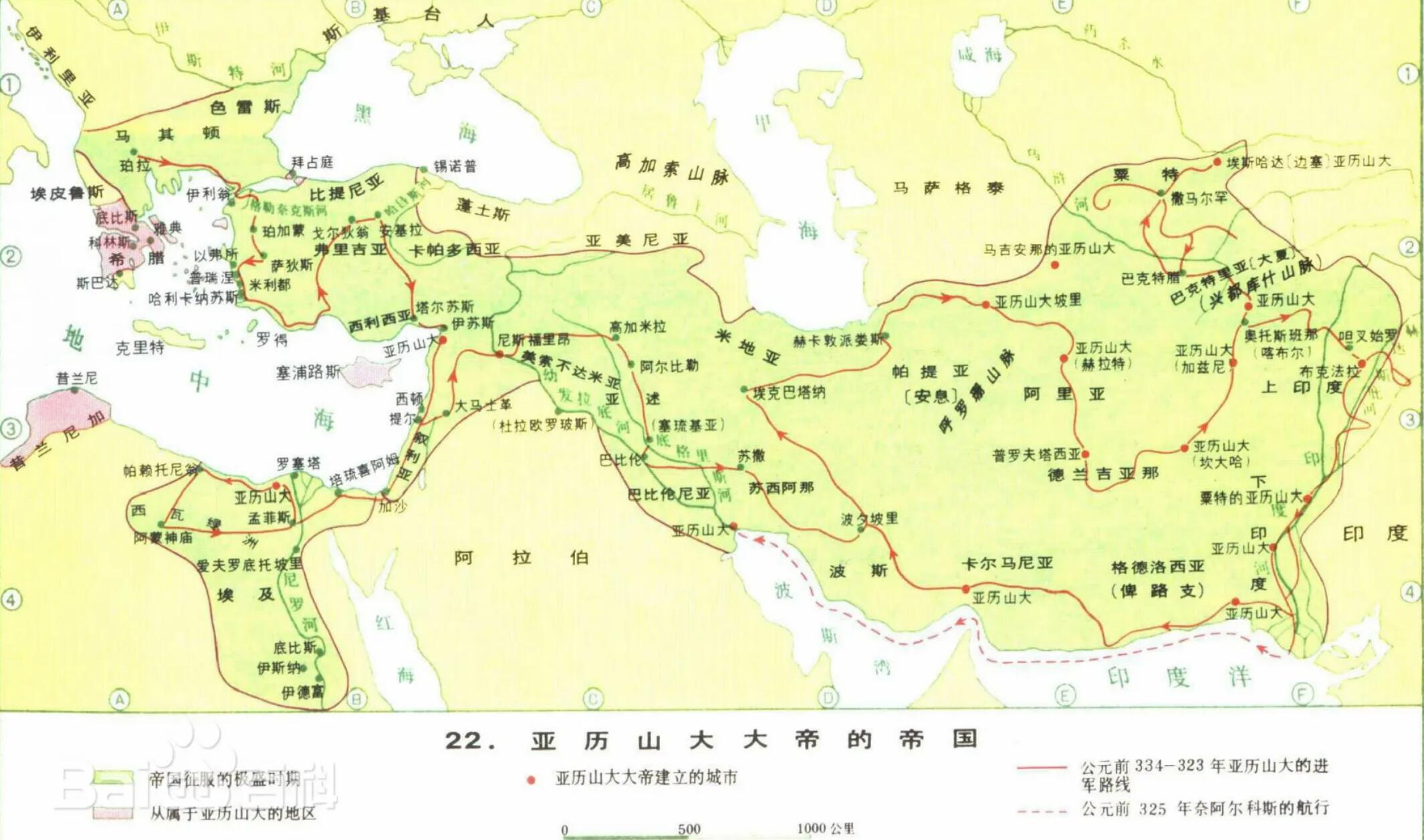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王耀武是一个比较精明也比较特殊的人物,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回忆:王耀武有自己的办公室,管着所有的学习小组组长,很多“同学”都想取代王耀武而成为功德林战犯中的“带头大哥”。
王耀武这个“带头大哥”并不是欺压“同学(功德林战犯互称同学)”的某“头”某“霸”,而是为战犯同学服务、帮管理人员做事的积极分子——战犯们在功德林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改造,王耀武的正式职务,是“学习委员”。
沈醉回忆:“王耀武越来越得到干部们的信任和同学们的尊敬,但这么多高级军政人员聚在一起,总有不少人对他这个委员眼红而想搞垮他取而代之。(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和文强口述自传)”
王耀武的地位确实令其他同学眼红,因为在一百多名将军级战犯中,“权力”最大的是学习委员王耀武,“权力”第二大的是生活委员庞镜塘,但是两人还是以学习委员为首:战犯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谁学习成绩好谁学习成绩差,王耀武有很大发言权和决定权,而庞镜塘这个生活委员,则有点“费力不讨好”。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有一间特殊的“工作室(实际是办公室,但不能那么叫)”专属于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庞镜塘和王耀武两人有一间小房子作为他们的工作室,各组学习组长与生活组长有事开会或碰头,便在这个房间内,别的战犯在他们不开会时,也可以去这里与他们聊天或反映情况。”
战犯们反映情况,当然是找王耀武而不是找庞镜塘,即使是找庞镜塘,也是发牢骚挑毛病,找王耀武则是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王耀武汇总上报,其意义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老王笔头一歪,好话能变成坏话,坏话也能变成好话,虽然王耀武从来都是实事求是,但是战犯同学们却不能不对他保持尊敬。
学习委员王耀武领导各个学习小组长,直接由管理所负责人(所长、政委,也就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的王英光、贺春年、胡大叔、马玉和那个级别)领导,每天学习完毕,王耀武都要召集各学习组长开一次碰头会,各组长向他汇报学习情况,由他汇集以后去向管理所的领导汇报。
据沈醉回忆,王耀武的确是认真负责如实地反映问题,所以他不仅得到管理所领导的信任,也得到所有的同学们的信任。 但是王耀武的山东同乡、同事庞镜塘(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老蒋任命的山东党务一把手),显然不具备王耀武的威望。
庞镜塘管生活,而那些被俘的高级将领好日子过惯了,再加上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这些高级战犯除了徐远举、周养浩、董益三等特务被抓时口袋空空之外,大多比较“富裕”:“因为解放军执行不搜俘虏的政策,被俘时身上带的财物都算是自己私有的,虽暂时交管理所保存,但随时可以取用。这些大官被俘时,身上往往带有大量美钞、黄金,所以花起钱来满不在乎。每逢年节,管理所同意买些香烟糖果食物时,有的一开口便是香烟10条、糖果10斤。”
沈醉在被俘时揣了十两黄金,被俘后又有很多“朋友”给他送钱,后来又从成希超藏在衣领、袜子里的两千一百美金中分得了三分之一(当年七百美金相当于六百多克黄金),所以花起钱来也毫不在乎,曾对他恨之入骨的徐远举周养浩,后来也吃他的最短,再也不骂他了。
战犯中的“财主”们上报的香烟糖果数量由庞镜塘负责统计并交由管理人员采购,再由她来分发。庞镜塘看着上千条香烟、上千斤糖果的采购清单也十分头痛,只好跟同学们“讨价还价”压低数量,结果引起了同学们的不满。
被庞镜塘压低了购买数量,有人十分生气地在他的办公桌上写了一首打油诗,直接把他气哭了:“前有石敬瑭,现有庞镜塘,现镜塘想学前敬瑭,可惜学不像!”
庞镜塘想让管理人员核对笔迹,找出那个恶作剧者,但是管理人员认为核对一百多人的笔迹动静太大而婉拒了。
还没找出打油诗作者,庞镜塘种在办公室的两盆山胡子(可能是山胡椒,根能之风湿)和五色朝天辣椒又被淋上了一大杯开水,等他发现这些东西蔫了的时候,已无法起死回生了。
庞镜塘再一次被气哭,他知道这件事不好再让管理人员调查,就请沈醉帮他“破案”,结果又被沈醉泼了一盆冷水:“我早不干这行了,这种案也不必去破它,你要反躬自问有什么地方使同学不满才是要紧的问题。”
现在想来,庞镜塘找沈醉“破案”是找错了人,因为写歪诗、浇开水这种事情,正规将军是不屑干的,那是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常玩儿的把戏,沈醉不但知情,而且可能是参与者——沈醉在回忆录中承认,他是经常去王耀武庞镜塘办公室抽烟聊天的。
与庞镜塘不同,王耀武只栽花不种刺,谁又不得罪,所以他从1956年转入功德林到1959年第一批特赦,一直稳坐学习委员办公室,连缝纫组长杜聿明对他也很是客气: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同学们经常称王耀武为“王佐公”,却没有人称王陵基为“王方公”、杜聿明为“杜光公”——蒋系高官都有名有字,取一字而称“某某公”是尊敬,比如白健公(白崇禧字健生)、李德公(李宗仁字德邻)、程颂公(程潜字颂云)。
因为王耀武很会做人做事,所以就成了功德林战犯同学中当之无愧的“带头大哥”:“管理所有什么事也由他向各小组去传达,大家对王也很信任,有什么思想问题不愿和小组长讲的,便和他去谈,这就比向管理人员去谈少了许多顾忌。”
王耀武第一批特赦后,每天早上再也听不到他高门大嗓喊大家“吃糖、吃糖(王口音很重,起床听起来就像吃糖)”,集合也不再由王耀武吹哨子——王耀武最后一次吹哨子,是1959年12月4日上午9点多钟,管理员叫王耀武吹哨全体集合时,人人喜形于色,列队进入小礼堂,礼堂主席台上挂的横幅“特赦战争罪犯大会”,那就是他们最后一次全体集合了。
王耀武离开了战犯管理所,谁会成为新的“带头大哥”,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杜聿明与王耀武同一批特赦,庞镜塘第二年也出去了,即使庞镜塘不出去,这个“老好人”也当不了大哥。
王陵基在所有战犯中军衔最高、年龄最大,但是他连自己都照顾不了,杜聿明出去后,胡子也不知道由谁来刮,所以他只能算“老前辈”,而当不了“带头大哥”。
在一百多名将军级战犯中,沈醉的年龄属于最小的一拨,他在杜聿明走后接任缝纫组组长,离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还有一段距离,徐远举和周养浩就更不用说了——这两个家伙在战犯中很不受待见,别说“带头大哥”,连小组长都当不上。
王陵基、沈醉一个太老一个太小,不想管事也管不了事,谁来充当管理所与战犯之间的联络人就成了问题,沈醉第二批特赦,后面的事情他不知道,自然也就没写,所以要找功德林战犯中的第二任“带头大哥”,我们就只能从其他“老同学”中去找了。
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人员名单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十分熟悉的名字: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
黄维这个人大家都比较熟悉,他就是那个“永动机研究家”,此人一向孤僻倔强,曾经挨过董益三(原军统电讯处少将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康泽的部下,跟沈醉同在第二批特赦)的耳光,他既没时间,也没兴趣“搭理”其他同学,同学们也不愿意跟他打交道。
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就是文强,但是有些事情刘安国在电视剧中能做(比如煽风点火说怪话),真实历史中的文强却绝不会做。
文强在战犯管理所虽然不认错,但也没有顽固反抗,在山东期间,他就是战犯中很重要的负责人,他在《口述自传》中回忆:“我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和看守员的关系搞得很好,后来所长换了人,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可能就是王英光的历史原型),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我每天忙得很,当学习组长,又管墙报,管文艺,我们自己还成立了一个图书馆,我又在这里负责,过年过节,还写些纪念的文章。”
战犯管理所的很多规定,也是文强帮着起草制定的:“他们把我写的一条一条规定贴在墙上,在我的房间里也贴上一条。这些条子贴起来,里面再没有哭的了,再没有吵架的了。还有一些年轻的管理员,有时我就跟他们讲:‘一方面你们当看守员,另一方面你们可以好好学习嘛,买些小学课本读一读,文化就慢慢提高啦。你们可以吹笛子,可以拉胡琴,学点东西嘛。’”
看过笔者前期文章的读者,肯定知道文强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他用领导语气跟管理人员说话,也是习惯使然。如果文强不转换阵营,其地位会高得难以想象。
文强最后一批特赦后,也进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当专员,而且成了专员中名副其实的负责人——当时王耀武已经辞世,文史专员办公室学习组长又全体专员选出,文强连续三次全票当选,做了十五年组长,专员们有什么事,都是请文强跟上面沟通,而且每次都是文强出马,马到功成,副组长沈醉跑前跑后给文强打下手,大家其乐融融。
文强为什么能成为新的“带头大哥”,除了他级别较高、办事比较有能力之外,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至于其他原因是什么,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可能比笔者了解得更清楚吧?
单字解释: 不 是 王 陵 基 更 不 是 黄 维 年 王 耀 武 被 特 赦 谁 是 功 德 林 战 犯 的 带 头 大 哥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历史迷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历史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